2020/11/26
〈上篇〉,1950年
那年秋天似乎走地特別早。
我急急忙忙地將三條蒸熟的番薯從家裡偷出來,在香氣尚未溢至阿姆的鼻孔裡,早就跑出家門外,無影無蹤。唇齒間的顫抖不曾間斷,狂奔帶來的熱氣似乎還是遠不及冬季的威力,但再不快些兒,就趕不到和姊姊約好的時間了。
還有茉莉姊姊。
茉莉姊姊是姊姊最近十分要好的朋友。她很漂亮,梳著一頭整齊的西式捲髮,及肩的髮梢總是對稱地翹著同樣的角度;五官標緻、面容姣好,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美人,村裏頭每戶人家都想叫自己的兒子把她娶回家;今天她穿著乾淨又柔軟的白洋裝,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材質,反正肯定是匹我們家買不起的高等布料,那領口還鏽著細緻的花邊,真是讓我打從心底的羨慕。還有茉莉姊姊她們家就像一棟精美的皇宮,是兩層樓高的西式洋房,她曾邀我們去玩過幾回,但姊姊和我每次總被眼前的氣派輝煌所震懾住,畢竟我們家的灶房比她家的練琴室還小得多呢。
不知道她和姊姊是如何結識的,可能是因為這一帶年紀相仿的女孩子只有我們吧。當我意識到時,三個人就經常在一塊兒說說笑笑、玩玩鬧鬧了。
「范玉霞,不是說別再拿番薯了嗎?都吃這麼多次了。」姊姊皺著眉頭。
「可是家裡現在只有這個……。」我有些委屈。
「不要緊啦,再嚐一次也無妨呀。來,這是南瓜糖。」茉莉姊姊溫柔地將糖遞給我們倆。在她帶來這麼多我不曾吃過的糖果西點中,我最喜歡這個南瓜糖了!外表平扁,一面紅、一面白,嚐起來非常香甜。
我們總是這樣互相交換各自帶來的零食,再一起坐在田埂間,邊談天邊享用點心,好不快樂!但常常覺得不太好意思,雖然是要帶「零食」,但我們家哪裡來的零食?只能偷些家裡的番薯充數,而且如果被阿姆發現的話,一定會被狠狠挨打;但茉莉姊姊不同,她經常帶來我們從未見過的點心,我們姊妹倆總像對待珍寶般,謹慎地小口小口品嚐。姊姊曾對我說過,茉莉姊姊的爸爸是律師還是老師來著,我忘記到底是哪個師了,反正印象最深刻的是,他能說著一口流暢又標準的日語,還有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,聽阿姆說那叫做福佬話。
在這短暫的偷閒時光中,是我們姊妹倆一天當中最期待的時刻。
「唉,秋菊,我最近不知怎麼了,覺得練琴愈來愈無趣。」茉莉姊姊嘆口氣,嘴角緩緩垂了下來。
「是嗎?可是妳彈得那麼棒,為什麼現在會覺得不好玩呢?」姊姊回。
「沒有啦,只是彈來彈去都是那幾種調子,聽都聽煩了。」
「不如,妳可以來試著彈彈我們客家的『老山歌』!」我突發奇想,興奮提出建議。
「什麼?那種歌一定不行用鋼琴彈吧?那可是西洋鋼琴耶。」姊姊沒好氣地笑。
「不!也許可行哦!」茉莉姊姊忽然站起來,雙眼睜得水汪汪又亮晶晶。
「真的嗎?」姊姊疑惑,抬起一邊眉毛。
「對!妳們現在就來我家,快唱給我聽聽那是首什麼樣的曲子!」她雀躍地在田野中跳著,好似一隻重獲自由的白蝴蝶。
姊姊清唱著,搭配茉莉姊姊的厲害的伴奏,實在相當新奇,我從沒聽過這般樣貌的老山歌,非常動聽。而且不僅她彈得優秀外,姊姊清脆明亮的聲音也十分搶「耳」,我老早就覺得她在歌唱方面擁有一定的天賦了。
「真棒!從來沒試過這樣的組合,好有趣呢!」茉莉姊姊的笑容非常燦爛,我在心中再次讚嘆著她的美麗。
「是嗎?妳開心就好。」姊姊也笑得甜滋滋的,好像撒了蜜在臉上。而且我剛剛就注意到,從開始歌唱至此刻,她的視線從未離開過茉莉姊姊。
「而且我直到今天才知道,原來妳有這般的好歌喉!以前妳從來沒和我提過唷。」她富有玩味的表情,逗趣地說。
「沒、沒有啦!又沒唱得多好。」她的兩頰上漸漸泛了紅,一副腆然。這是我從未見過的樣子。
「既然這麼會唱,那我要教妳代表『我』的曲子哦。」
「代表妳的曲子?」
「妳可要好好唱,這是我的最愛呢。」
“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,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
芬芳美麗滿枝枒,又香又白人人誇
讓我來,將妳摘下
送給別人家
茉莉花呀、茉莉花“
「請問美麗的『茉莉』小姐,為什麼要把『妳』送給別人家呢?」姊姊刻意在「茉莉」加重了音調,俏皮地問。
「我也不知道,但我可不要亂送到別人家哦!」茉莉姊姊笑嘻嘻回應。
颯颯北風聲越強,距離迎新年就越近了。家裏頭愈來愈需要人去打點、準備過年,姊姊和我即被命令做各式各樣的粄:發粄、紅粄、菜頭粄……,好來祭祀祖先與分送親戚,祈求過個好年。所以我們能和茉莉姊姊見面的天數就逐漸變少了,但奇怪的是,見面時,她們倆也經常只是並肩依偎、遠眺晚霞,又時不時轉過頭來,靜靜地凝視著對方,偶爾臉上掛著笑,但總覺得和從前不同──像株盛開的花朵逐漸枯萎凋零的模樣,有股哀愁在她們的臉上揮之不去。甚至曾經有一回只有點個頭打招呼,就沒說任何話了。我曾懷疑過她們是吵架了嗎?但吵架的話為何還要繼續見面呢?追問姊姊,她又只說沒發生什麼事,我不知道她們到底在想什麼。只明白我與她們的距離好像愈來愈遠,即使坐在旁邊而已,卻好像天涯和海角般的遙遠。她們似乎建了一座專屬於她們的國度,有著隱形卻又堅固的城牆,不許其他人輕易闖入。
直到有天,她們那座王國也無聲無息地消失不見──茉莉姊姊他們一家離開了。
阿姆是說茉莉姊姊她爸爸安排一個好人家,聽說是日本留學回來的醫師兒子,就嫁去大臺北跟著過生活了;但住在隔壁的姨婆卻說,瞧見好幾次警察大人前來他們家,大人有著濃厚的外省口音,滿臉怒容的大聲斥責么喝,甚至還闖入他們家中,翻箱倒櫃的聲響隨之傳來;有人附和著,但又傳說著是她爸爸的事業出了問題,要全家找個新地方去避避風頭。五花八門的傳言在村裡流竄著,誰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。
大家只確定,那朵如茉莉花嬌滴的美麗女孩,是永遠離開這兒了。
我曾偷偷問過姊姊好幾次,關於詳細的原因她知不知情?只見她每次都繃著臉搖搖頭,不曾為此發過一語。過了好些日子,即使姊姊的臉上重新浮現了笑顏,但是我總認為在這張面容之下,她小心翼翼地藏著不為人知的哀痛與酸楚──就算其他人未曾發覺過。
我仰著頭,眺望那橙紅的天色,明明不久前才三人一起看過,但現在卻好像被染上腥紅的鮮血,有股不舒服的感覺從我身體深處直竄上來,蔓延至全身。我馬上轉頭想問姊姊有沒有同樣的感受,但才張開口,我就把嘴閉上了。
姊姊靜靜蹲在那方形白瓷的盆栽旁,眼前綻放著滿叢的茉莉花,花香撲鼻、嬌嫩欲滴。那是茉莉姊姊在去年秋天送給姊姊的生日賀禮,從未慶祝母難日的姊姊雖然再三推辭不能拿,但還是被強制要收下了。
「雖然妳是『秋菊』,但每個人都送菊多無趣呀!但若是『茉莉』的話,肯定令人覺得高雅又新奇。」那時的茉莉姊姊感覺比姊姊還要高興,難得像個樂壞的小孩。
「而且妳每次看見它,就一定能想起我。」
姊姊的目光呆滯,是賞花賞出神了?她緩緩伸出手,將一株下垂的花苞捧在手心上。「是不是六月雨下得不夠?妳怎麼還沒盛開呢?」她溫柔地說,像呵護嬰兒般的輕聲細語,再輕輕柔柔地哼起那首歌──她好久不曾唱她了──《茉莉花》。
此時,我的眼眶有些濕潤。我不忍心提醒姊姊,上個月的夏雨是如此滂沱、豔陽是那麼盛大。有些事物本來就會脫離自然法則,並不需要其他特別的原因。
我想,那朵茉莉是不會開的了。
〈下篇〉,2020年
起風了,姊姊的白色蕾絲紗裙也隨著逐波擺動。
已近典禮尾聲了,但姊姊還是不肯把婚紗換掉,她說一生大概也只有一次能好好地享受這樣的精緻儀式感,所以就讓她徹頭徹尾、好好沉浸在其中吧。但郁芯早早就換上輕便的無袖長洋裝了,那墨綠的衣料十分雅緻,像她眼睛的顏色。
今天天氣還算不錯,陰陰涼涼,標準的新竹秋天,而且還好沒下雨,不然不知道姊姊她們的大喜事會有多掃興。她們的婚禮不是舉行在一般人常去的婚宴飯店、而是在草地上,像辦個溫馨野餐的小聚會。沒有邀請額外雜七雜八的人、那些連她們自己都認不出是哪位不熟的親戚,只有親密家人與三五好友,連司儀和奏樂也都是我們熟識的老鄰居。
一切感覺都很棒、很愜意。
「喂,陳曦,什麼時候換妳要嫁掉啊,如果再這樣下去可就變成老剩女了哦!」姊姊搖搖晃晃地對我喊,不知道她灌了幾杯酒下肚,醉意湧在那張嬰兒肥的臉龐,眼睛裡卻清晰地映著滿溢的喜悅。
「妳倒不用管我,就算我變成老剩女我也開心。」我說。
「好啦,妳也知道她酒量很差,別在意哦。」郁芯在旁攙扶著她,帶著些許虧欠的眼神對我說。明明已經過快三小時的婚禮,但我絲毫都不覺得她的面容帶有一絲倦意,而且不論看幾次,我都覺得她五官長得好精緻。真漂亮。
「我知道的。」莞爾。
「阿婆呢!阿婆怎麼還沒來!我要等阿婆來才准放大家回去哦!不然誰都不能先跑!」姊姊突然高分貝尖叫,是發酒瘋還是真心話我實在有點分不清。
不過阿婆到現在還沒來的確令人有點擔心。聽爸爸說今早她的老毛病又犯了,實在沒辦法準時來姊姊的婚禮,等她恢復些會叫叔叔趕快載她到場的。我相信阿婆最後一定會到的,因為她最疼姊姊了。
真的,「最」。
姊姊在家中剛出櫃的那陣子,真是滿屋子的烏煙瘴氣。爸爸雖然都不怎麼說話,但默默遞了張名片給她,上面是他大學同學的名字──在臉書好友標記上曾瞄過幾眼,但刺眼不是名字而是那三個大字──「精神科」。而媽媽則把日子過得像是用眼淚洗出來的,吃飯哭、睡覺哭、連看電視握著遙控器的時候也哭。只有阿婆,在今年過年眾多親戚七嘴八舌議論著姊姊的時候,一句:「細人仔歡喜就好、大人莫管佢恁多。」打破吵雜,同時也縫上眾人的嘴。
因為這樣,現在姊姊才能快快樂樂地牽著心愛的人,在這和大家共襄盛舉她們的喜悅。
一切光明正大、坦坦蕩蕩。雖然本來就沒有做錯什麼事情。
「所以阿婆怎麼到現在都還沒來?」我繞到爸爸身旁,悄悄問。
「應該快來了,剛剛阿文叔打了電話,說她的精神好多了。」
半晌,阿文叔就緩緩地將把阿婆推進來,而就算只能坐在輪椅上,誰都看得出她今天一定經過了極用心的妝扮──說不定已經好幾十年沒這麼做過:細細的淺棕色彎眉、嘴上擦了些殷紅色胭脂、還有那雙眼──明明沒抹上什麼眼影那類玩意兒的化妝品,但我總覺得那格外的明亮有神、目光炯炯。她身穿的那件紺青色的套裝是我未曾見過的,但阿婆不太可能輕易地就買件全新的衣裳,她總捨不得。所以,應是從她那玫瑰木衣櫃取出的,裏頭承載了許多她沉睡已久的年輕回憶。
阿婆她其實有個很文雅的名字,秋菊。西風瑟瑟中,更覺得多了份美麗的惆悵,雖此風非全然意味著淒涼,但在這季節裡,愁緒反而使人更增了一種哀艷的氣息,帶著淡淡冷空氣的味道。
阿婆一到,眾人忙著齊向她招呼問候,也把許多替她留著的山珍海味一一端上前來,但只見她微笑搖搖頭,以客語說:「𠊎食毋慣,你兜食就好。」阿文叔忙著接話:「剛剛阿婆有吃了,她是特地來看怡寧的。」
「阿婆!特地來看我哦,這樣郁芯會偷偷難過哦。而且我一定要給妳看我穿婚紗的樣子!沒有沒漂亮呀?」姊姊一看到阿婆被團團圍住,馬上衝過破人群,向她連珠炮似的撒嬌。
「真靚,最靚个新娘!」阿婆開心到眼角都拉出好多條魚尾巴了。
「阿婆,之前不是答應我要在結婚那天獻唱給大家聽嗎?等妳等好久了哦。」
「聽老人家唱歌,眾人恁無聊。」
「唉唷!阿婆的歌喉這麼好,全場誰不知道呀?妳就唱妳最喜歡的那首歌,開心就好呀!」
的確,阿婆的好歌喉是眾所皆知的。雖然平常沒提起,但只要在大家面前開過一次金嗓,在場的人都肯定會記住她的聲音──清雅、婉轉、又動人,像天還沒亮時,停在葉梢的清澈露珠。
“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,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
芬芳美麗滿枝枒,又香又白人人誇“
「陳曦,妳覺得同性戀會遺傳嗎?」姊姊說。眼神渙散,但是嘴角上揚。
「妳在講什麼啦,怎麼可能啊。」我回。
「沒有啦,我只是覺得,阿婆看起來好像快哭了一樣。說不定她年輕時比我還會撩妹哦。」
「妳到底在講什麼啊?阿婆喜歡女生?」
「對啊,不覺得很像嗎?好想看阿婆的女朋友哦,一定很正!說不定阿婆的女朋友就叫做茉莉,或是她最喜歡的花是茉莉花啊?不然她怎麼這麼愛這首歌,又沒多好聽。」
「妳才一點都不懂得什麼叫好音樂哩。」
「最好是啦。」
從沒想過的問題,突然從腦袋浮起──好問題耶,阿婆真的喜歡過女生嗎?那為什麼還要跟阿公……?好吧,從前那時代好像不這麼做,真的會被家裡打斷狗腿吧,或是比這些都還嚴重的事情,是我現在所無法想像的。
突然好感慨,或許還是時常在怨嘆臺灣這塊土地上,發生那麼多令人灰心喪氣、難以接受的事情,但其實、其實──也是如此溫暖的小島。是啊,可以在這裡結婚了、能光明正大將愛人的名字印在自己的身分證背後了,已經過一年多了。
時空如果允許的話,把這些都倒回阿婆的青春裡,那又會發生什麼事呢?
周遭人群鼓吹著阿婆安可,打斷內心的自言自語。我望向她,那張佈滿光陰痕跡的臉龐,散發著無止盡的溫柔。她用那雙被歲月風霜刻劃的手,再次取下麥克風。
一樣是那首,她最愛的《茉莉花》。
這回我全神貫注地聽著,也深情地望著阿婆。她剛唱第一次時是那麼喜氣洋洋,但現在總覺得添了一份道不出的淡淡哀傷;她的眼睛真如姊姊所說的、淚光閃閃。是因為姊姊結婚而感動嗎?還是為那位我無從得知的美麗女孩?
“讓我來,將妳摘下
送給別人家“
“茉莉花呀、茉莉花“
這次,不只是阿婆,連我的眼裡都盈滿了淚。
或許等到下輩子,就能細細呵護著那朵她最寶貝的茉莉花了。
──獲2020高科大文學獎短篇小說組第一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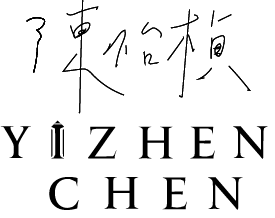
i love this greatest artic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