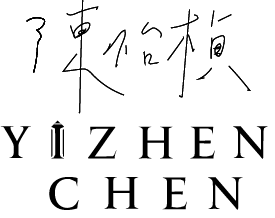2022/08
「編,將物交叉組織,使其聯結與綴合。」
一個戴著深卡其色牛仔帽的爺爺坐在樹下,襯衫整齊的扣好到最上面,他充滿朝氣的向我們揮手,墨鏡映著盛大的陽光、閃閃發亮──
他是Sawmah,阿美族人,漢名吳阿春。
他是頑強的野藤,沒有離開過滋養自己的土地、遇強風及暴雨也不曾枯萎落地。那是在襖熱的東海岸邊、在一個個平凡而踏實的春日裡。
現今已八十七歲高齡的Sawmah,從前在這被選為頭目長達三十二年,從此處我們能一窺族人對他的喜愛與尊敬。在他年輕時捕魚、務農、蓋房樣樣行,而從七十歲之後開始他的編織之路。他細緻的編器作品也慢慢被愈來愈多人認同與肯定,逐漸成為豐濱鄉當地重要的編織耆老之一。
「我要努力試著把家庭站起來看看。」
人們總想睜大眼、拼命張望,希望能窺見最遠的天邊和海上。但他年輕的時候似乎不是這樣,不追求最高、最遠的盡頭,只為了家庭與生活,專注單純地打撈眼底的每一隻魚、九孔或龍蝦。
「龍蝦在這裡,一公斤130塊;賣到花蓮市,一台斤1000多塊。」他說。
不是用族語來表達,可能不太精準和到位,但他仍努力以不怎麼流利的中文和我們對話。但是,我並不覺得這會是隔閡。因為從他純樸的眼睛裡,我能看見眼裡深處高漲的情緒──可能是無奈、憤恨、委屈,或全交織編雜在一起。
那不需要透過言語,彼此都能明白的事情。
「真的不能回頭一直想以前,眼淚會掉下來。」他的太太Kiniw也這麼說。
她從年輕時就一肩扛下經營雜貨店的生意。但是,從一個世代務農家庭長大、一開始連計算機也不會打的傳統女子,經營之路的開端吃足了苦頭。從前客人喜歡賒帳、不懂經營但必須經營,她咬牙苦撐,半夜被路過的卡車運將敲敲門,她還是替他們以煮一頓飯,為的只是賺那三、五十塊。
「以前娘家很苦、結婚後也苦,我不要我的下一代也這麼苦。當時我很好奇為什麼人家可以有土地有錢,那我也來打拼看看──」
「我要努力試著把家庭站起來看看。」
訴說這些往事,她的眼眸好像會閃爍。Kiniw最後考取了廚師執照、還到台北比賽得獎,或許這些真能證明,辛苦的代價最後真的會還給她、與她的家庭吧。
生活縫隙裡的技藝與記憶
當抬頭看見頭目海產店裡看見擺放著他親手製作的各式編織器物,它們是如此小巧而精細。我們詢問faki跟誰學編織的,他睜大眼睛,表情有些理所當然,但又富有些許玩味和驕傲:
「自己看、再自己學的啊!」
還是睜大著眼睛,不過這次是我們。無師自通、沒有禁忌。在退休以前,他為了家庭生活而上山下海的打拼,所以七十歲才開始編織之路。我們好奇著,是因為從前就對編織很有興趣,所以之後才開始做嗎?
「人家喜歡要買的話,我就賣。」
「但我也不是希望要賣。」
苦思著要如何了解耆老的編織心境,於是我一個人站在海產店裡,近乎於肅立的姿態,靜靜端倪他親手做的每一個編器:faroro(背簍)、karihic(魚簍)、fakar(魚笙)……。物件不會說話,但我卻好像聽聞到好多聲音與氣味:外頭傳來faki和親朋好友歡樂談天、新鮮海產剛起鍋的熱熱香氣,我輕輕撫觸和觀察一節一節細膩的痕跡、每條藤條上與下連結之處……,不必說話,所有的細膩與精緻已經透過器物本身即嶄露無遺。這時,忽然好像能稍微明白faki的心境──無師自通,以眼、用手及心,做好每一個編器。不全為喜歡或錢財,只因為「生活所需」、進而「動手去做」,以此交織起每個日常的片段。
或許,就是如此單純而已。
編織,以優雅、內斂的古老編織技法,串接起的不只是植物本身,更將他們日常事物緊密的綴合、連結在一起,只專屬於阿美族人生活的技藝與記憶。而他會一直在那。faki向我們揮手道別,他眼角笑開的魚尾紋如花綻放、他的編器會繼續安安靜靜地跟隨著他們的日常裡──
屬於他、屬於磯崎,也屬於阿美族人生活空間的每一個角落。
在生活的隙縫裡,正悄悄地綻放硬朗的藤花。
──收錄於《「豐濱製造」原住民編織工藝師圖冊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