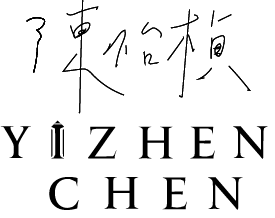2022/08
門外的陽光穿透屋內,在她雪白的睫毛灑上淡淡金黃。
熠熠發光,這是我第一次看見銀色的睫毛。她的視線沒有對焦在手中的線,但指尖卻飛快地動作、搓捻出一綹綹的纖長與細緻。我很難想像眼前這幅畫面,竟來自一個上百歲的長者。 那是整整閱歷一世紀的人哪。
□
噶瑪蘭的日子
她是Api(漢名朱阿菊),噶瑪蘭族,生於1920年,已達102歲超高齡。為花蓮豐濱新社部落十分重要的香蕉絲編織耆老,在六年前榮獲花蓮縣政府文化資產「噶瑪蘭香蕉絲編織工藝」之保存者。從民國十年出生到現在,她從來沒離開過現在所居住的這間老地方。「以前這裡沒有馬路,只是一條寬寬的草地路。只能供行人使用、車輛無法行走。而且,家裡以前還是茅草屋」,根據Api的八女兒邱慧玲所說,她對於小時候居住在茅草屋有個印象特別深刻──
牆壁是用牛糞砌成的。
從前大部分人家都有養牛,在一大早,大人小孩都會去蒐集牛糞,然後開始加水進去混和,沒有混任何的泥巴。等待一段時間後,就開始如舖地般的築牆。而且,這種用牛糞砌成的牆壁,聞起來並沒有任何臭味,實在是讓小時候的慧玲覺得很神奇。此外,她還分享噶瑪蘭族語的「simpaliw」,指的是換工、全村的人會在某戶人家需要幫忙時全員出動。例如今天這戶人家要插秧割稻,全村就會一起幫忙;明天換那戶人家要蓋房,明天大家就前去互助。這就是simpaliw。
我覺得好友善,好溫暖。
而Api的媽媽是噶瑪蘭族人、爸爸是撒奇萊雅人,而她的先生邱庭章則是位客家人。在如此多元的環境下生活,因此她擁有一項讓我們感到非常佩服的技能── 她竟然會說七種語言!
噶瑪蘭語、撒奇萊雅語、阿美族語、日語、客家語、閩南語、華語。「我媽媽的日語不是那種只會幾句的哦,她的日語嚇嚇叫。」慧玲補充。
在訪談的過程中,的確能聽到Api一下子說噶瑪蘭語、一下子又切換成流利的閩南語。我除了萬分佩服之外,也感到有些內疚。先不談其他的語言熟不熟練,連自己的母語客家話都沒辦法講得非常順暢。她以自身再次深深提醒我,要好好學習與珍惜,「記得要會說自己的的話」。
「她最特別之處,在於『線很細』。」
除了語言的學習能力高強,Api最廣為人知的厲害技術當然以「香蕉絲編織工藝」莫屬。在她五十歲左右,當時開始推行傳統文化保存的相關運動,因此開始編織。而她驚人的學習能力在此處大大綻放──無師自通,只憑自己過人的觀察能力、以及靈活的巧手,即編織出一個個精細雅緻的作品,讓人非常敬服。
以「香蕉絲」作為編織材料使用,也是噶瑪蘭族一項極大的特色、具相當高的獨特性。而根據文獻紀錄,傳統的香蕉絲編織所使用之蕉種屬於北蕉品系,植物高大、原多供以食用。而噶瑪蘭人經常以被風雨吹倒、受到災損的香蕉樹假莖作為材料,在此體現族人與自然共處及惜物精神。但是,也並非所有假莖都適合作為織物的原料,可使用與否、編織用途,皆須依靠編織耆老長年累積的經驗去做判斷與挑揀。
接著,慧玲拿出幾個媽媽以前的作品「lumus」(可以用來裝檳榔的小包袋),她說上頭米白色的部分即是媽媽用香蕉絲親自編織而成的,非常細緻。
「她的編織跟人家最不ㄧ樣的地方,在於她的『線很細』、『工法很細』。」
輕輕撫觸著布料,我的確感受不太到在哪邊是接線處,非常平整,打結的地方也幾乎小的摸不見。慧玲還提到,為了節省線,她打結的長度也很短,差不多才1.5公分,即為手捏起來剛剛好的寬度。
線很細、結很小、工法很精緻。真是又欽佩又讚嘆。
對於編織這麼精細要求,或許這與她平時做事的個性也有所相關。慧玲說媽媽平時就非常愛乾淨,即使到現在年紀這麼大、行動很吃力,但在進房前總會記得脫鞋。我也相信,一個人的性格會在每件事情上展現,哪怕是再枝微末節,那是自己身體與心的記憶。
身體會記得
後來,我們請Api為我們現場示範編織,但因年紀已大、身體逐漸退化,現在只能pemuliz(結香蕉絲)整理線材。我非常專注地盯著她手中的線,動作十分迅速,完全不像是一個上百歲的奶奶會有的靈敏。我近距離觀察她的眼睛,眼睛其實沒有對焦,我才想到慧玲剛剛提過現在她已經幾乎聽不到、也看不太見了。那麼,她是怎麼辦到的?
「她記憶還很好,身體也都記得。」慧玲默默說,好像能偷聽見我的心聲似的。
我看著Api的表情,比起先前訪問時間過長,可能有些疲倦、沒有精神;而現在她一拿到線,和剛才的面容截然不同,好像帶著十足的自信與滿足,容光煥發。而且在這麼近的距離,我看見她已全白的睫毛,灑上了門外穿透進來淡淡的金色陽光。
好美麗。
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,一定很幸福吧。
幾年前,當時Api身體狀況還不錯,還能去附近的光織屋當編織講師、也有一些學生專門前來向她請教。只是現在身體退化許多,已經沒辦法再出門走走、也沒有體力跟耐心去教導了。
「我還記得,以前媽媽還常常覺得我們很遲鈍,明明就已經教過這麼多次,怎麼還是學不會。」
「因為她是自己看、自己學,沒有老師教她咧!」慧玲笑著跟我們分享。
採訪尾聲,我們問Api,有沒有什麼話想對現在想學編織的年輕人說呢?
她只強調她都還記得怎麼織,只是現在已經沒辦法做了。接著,一直重複呢喃現在仍會香蕉絲編織的那幾個人,如同點名。即使她沒有全然表達出她對編織的心情,但從她一直重複講述的人名裡,我能隱隱感受到,還是很在乎這項技藝會不會消失吧。而慧玲其實也想學好好學習編織很久了,但一直都沒有機會能夠去實踐,這次回花蓮希望能夠能不能學得學精一點。
「我不敢說傳承文化,但我的確想把這項技術學起來、把它保留下來。」
「如果最後沒有了,不是很可惜嗎?」
□
準備道別的時分,她慢慢從椅子起身,背對我們、一步一步緩緩往她的房裡走去。小心翼翼,進房不忘要脫鞋。離去的空座位,留下她剛剛pemuliz捻好的絲線,整齊的圍繞成一圈線球。還有她米白色的lumus倚靠椅背站立,直挺而溫潤。像是留下的痕跡。
是個雪亮的祝福吧。
──收錄於《「豐濱製造」原住民編織工藝師圖冊》